納蘭性德,原名成德,字容若,號愣伽山人,滿州正黃旗人。十七歲進太學,十八歲中舉,二十二歲中進士。授予三等侍衛之職,後晉二等,不久再遷一等。二十三歲開始扈從康熙巡視,並於康熙二十一年,隨副督統郎談等人奉使覘梭龍,勘查黑龍江及雅克薩城一帶的形勢,足見康熙對他的器重。
十九歲時娶兩廣總督、兵部尚書督察院右副督御史盧興祖之女為妻。葉舒崇所撰〈皇清納腊室盧氏墓誌銘〉記載纳兰容若:「夫人盧氏……其父興祖,總督兩廣兵部右侍郎,督察院副督御史……夫人生而婉娈,性本端莊,貞氣天情,恭容禮典……年十八,歸於同年成德,姓納腊,字容若。
……康熙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卒,春秋二十有一,生一子海亮。容若身居華閥,達類前俢,青眼難期,紅塵寡合,夫人境非挽鹿,自契同心……於其歿也,悼亡之吟不少,知己之恨尤深……」可見盧氏十八歲嫁予納蘭性德到二十一歲去世的三年多之間,夫妻情感甚篤,納蘭性德更將盧氏引為知己,故盧氏的逝去,給他帶來莫大的打擊,因而「悼亡之吟不少」。
納蘭性德與盧氏少年夫妻,驟然死別,他從最初的哀痛欲絕,轉向宗教尋求慰藉,甚至盧氏死後的七、八年,深刻的思念依然不變。儘管續娶官氏,又納妾數名,仍然無人能取代盧氏在他心中的地位。故試就納蘭性德於盧氏亡故後心情轉變的三階段,來探討其悼亡詞。
(一)悲愴淒惻期:盧氏歿後,納蘭性德哀淒無限,悲傷無法抑制,源源湧出而為詞作。如自度曲〈青衫濕遍?悼亡〉:
青衫濕遍,憑伊慰我,忍便相忘。半月前頭扶病,翦刀聲,猶共銀釭。憶生來,小膽怯空房。到而今,獨伴梨花影,冷冥冥,儘意悽涼。
願指魂兮,識路,教尋夢也回廊。 咫尺玉鉤協路,一般消受,蔓草斜陽。判把長眠滴醒,和清淚攪入椒漿。怕幽泉,還為我神傷。道書生,薄命宜將息,再休耽怨粉愁香。料得重圓密誓,難禁寸裂柔腸。
對納蘭性德而言,盧氏不單是妻子,更是知情解意的伴侶。
想到半月前仍操持女紅的妻子,轉瞬間陰陽兩隔。更希冀能用淚水把妻子滴醒,卻又怕在黃泉之下的妻子為他擔心。想起妻子生前的勸慰、訣別的情景,及來生誓約,不禁柔腸寸斷,哽咽不語。納蘭性德對於喪妻的巨大打擊,心理不能馬上接受,總有種游移虛實之間的矛盾。
如〈南鄉子?為亡婦題照〉:
淚咽卻無聲,止向從前悔薄情。憑仗丹青重省識,盈盈,一片傷心畫不成。
別語忒分明。午夜鶼鶼夢早醒。卿自早醒儂自夢,更更,泣盡風前夜雨鈴。及〈虞美人〉:
春情只到梨花薄,片片催零落。
斜陽何事近黃昏,不道人間猶有未招魂。
銀箋別夢當時句,密綰同心苣。爲伊判作夢中人,索向畫圖影裡喚真真。
納蘭性德希望通過為亡妻畫像來慰藉自己悲切的心情,可是盈盈淚水遮住了視線,傷心難畫愛妻容。甚而期望人間真有招魂一事,使妻子復生。
及至畫成,向畫中人呼喚她的名字,願如傳說中的真真一般,從畫中走出。並將寫有當年定情詩句的紙箋,打上同心結,以示對妻子的愛不變,讀來令人鼻酸。其實作為王公貴子的納蘭性德,移情他物或另結新歡,本是易如反掌,然而夫妻間深厚的情感,使他生活在夢幻之中,苦苦折磨自己。
康熙十六年(1677年)重陽日所作之〈沁園春〉是納蘭性德悼亡詞之代表:丁巳重陽前三日,夢亡婦澹裝素服,執手哽咽,語多不復能記。但臨別有云:「銜恨願爲天上月,年年猶得向郎圓。」婦素未工詩,不知何以得此也,覺後感賦長調。
瞬息浮生,薄命如斯,低徊怎忘。
記繡床倚偏,竝吹紅雨;雕闌曲處,同倚斜陽。夢好難留,詩殘莫續,贏得更深哭一場。遺容在,只靈飆一轉,未許端詳。 重尋碧落茫茫。料短髮,朝來定有霜。便人間天上,塵緣未斷;春花秋葉,觸緒還傷。欲結綢繆,翻驚搖落,減盡荀衣昨日香。真無奈,把聲聲鄰笛,譜出回腸。
開頭便以痛惜之語對亡妻發出感概,思緒禁不住勾起回憶,展示往昔少年夫妻嬉戲悅情、打鬧廝玩的美好情景,夢醒人去,更顯今日之愁苦,致使鬢添霜絲。只是春花秋月,到處都會觸痛心中悲傷,只好藉笛聲來寫出一字一淚地哀悼。
納蘭性德因夢中情景的觸發而作此詞,有感而發、不吐不快的創作動機,亦是此詞動人之處。
(二)宗教慰藉期:納蘭性德青春時期「當花側帽」的明快心境,已隨盧氏的亡故一去不返。為了從這種無力自拔、消耗心力的悲苦中解脫出來,納蘭性德轉向宗教以求出路。
但在宗教中,他所找到的並非是解脫,而是走向消極的否定人生。如〈眼兒媚?中原夜有感〉:
手寫香臺金字經,惟願結來生。蓮花漏轉,楊枝露滴,想鑒微誠。 欲知奉倩神傷極,憑訴與秋檠。西風不管,一池萍水,幾點荷鐙。
〈金縷曲?亡婦忌日有感〉:
此恨何時已。
滴空階、寒更雨歇,葬花天氣。三載悠悠魂夢杳,是夢久應醒矣。料也覺、人間無味。不及夜台塵土隔,冷清清、一片埋愁地。釵鈿約,竟抛棄。 重泉若有雙魚寄。好知他、年來苦樂,與誰相倚。我自終宵成轉側,忍聽湘弦重理。待結個、他生知已。還怕兩人都薄命,再緣慳、賸月零風裏。
清淚盡,紙灰起。
盧氏去逝已三年,但納蘭性德的悲痛之情未減,開始覺得活在世上沒什麼意思,不如去九泉之下,實現釵鈿之約。他希望知道妻子在幽冥的生活是否安好,並說明自己並無續弦之意,只願與妻子再續舊情,卻擔心兩人緣分淺薄。
納蘭性德叨叨絮絮地向亡妻一訴三年來的苦悶,流露出一片真情,使人不忍卒讀。
〈憶江南?宿雙林禪院有感〉
心灰盡,有發未全僧。風雨消磨生死別,似曾相識只孤檠,情在不能醒。
搖落後,清吹那堪聽。
淅瀝暗飄金井葉,乍聞風定又鐘聲,薄福薦傾城。
納蘭性德本已孤處獨棲,死別之恨難以排遣,而當此暮秋時節,梧葉飄零的悽涼之聲與寺廟的晚鐘聲此起彼落,使他心煩意亂,無法忍受。其實納蘭性德的萬念俱灰是由於對亡妻鍾情太深,故仍在情海中浮沉,無法像高僧般六根清淨,大徹大悟,因此將亡妻的死歸咎於自己的福薄。
此乃情深之極、沉痛之極的感喟、怨責。
(三)平淡思念期:此時納蘭性德的悼亡語氣已不再如先前那樣激切淒厲,而變得異乎尋常地平淡和沉靜。如〈少年游〉:
算來好景只如斯,惟許有情知。尋常風月,等閒談笑,稱意即相宜。
十年青鳥音塵斷,往事不勝思。一鉤殘照,半簾飛絮,總是惱人時。
〈采桑子〉:
謝家庭院殘更立,燕宿雕粱。月度銀牆,不辨花叢那辨香。 此情已自成追憶,零落鴛鴦。雨歇微涼,十一年前夢一場。
〈鵲橋仙〉:
夢來雙倚,醒時獨擁,窗外一眉新月。
尋思常自悔分明,無奈卻、照人清切。 一宵鐙下,連朝鏡裏,瘦盡十年花骨。前期總約上元時,怕難認、飄零人物。
用「夢」與「醒」作對比,謂夢中與亡妻並倚欄杆,如今卻獨自擁衾而臥,愁思躍然紙上。對於過往的事,想忘卻不能,對鏡含悲,玉肌消瘦。
多年的漂泊風塵,形容憔悴,縱使再相見,怕是「對面不相識」了。
這是納蘭性德最為人熟之的詞風,不侷限於悼亡詞,只是在悼亡詞中表現得更為明顯。如〈南鄉子?為亡婦題照〉:「午夜鶼鶼夢早醒。卿自早醒儂自夢,更更,泣盡風前夜雨鈴。
」將死亡比喻為夢醒,可見他的心如槁木死灰,了無生趣。此外,也用了許多的「愁」、「悲」字,如〈琵琶仙?中秋〉:「愁中看,好天良夜,知道盡成悲咽。」、〈蝶戀花〉:「唱罷秋墳愁未歇,春叢認曲雙棲蝶。」有時也直接點出「淒涼」、「傷心」、「斷腸」等語,如〈鵲橋仙?七夕〉:「乞巧樓空,影娥池冷,說著淒涼無算。
」、〈青衫濕?悼亡〉:「近來無限傷心事」。愁緒難遣,使納蘭性德的詞中,充滿大量的「孤」、「獨」、「空」、「冷」等字樣,如〈沁園春〉:「夢冷蘅蕪,卻望姍姍,是耶非耶?」、〈紅窗月〉:「道休孤密約,鑒取深盟。」這種孤單落寞、冷清寂寥的氣氛縈繞在字裡行間,婉約之中,更覺苦澀淒涼。
納蘭性德以自然真切的口吻,抒寫心靈感受。如〈青衫濕?悼亡〉:「近來無限傷心事,誰語話更長。」、〈鵲橋仙〉:「夢來雙倚,醒時獨擁,窗外一眉新月。」、〈尋芳草?蕭寺紀夢〉:「若不是恁淒涼,肯來嗎?」語氣的轉折十分順暢,明白如話,彷彿隨口道出。
至於疊字,詞作中亦使用普遍。如〈生查子〉:「教盡厭厭雨」、〈浣溪沙〉:「蕭蕭黃葉閉疏窗」、有時是疊詞的使用,如〈采桑子〉「惆悵離情。莫說離情,但值涼宵總泪零。」、「那是今生。可奈今生,剛作愁時又憶卿。」重詞疊字的使用,一方面能加強詞的音樂效果,既順口又容易記憶;一方面在三強調想要表達的重點,使意象更為突出。
納蘭性德很少使用僻典,語言也明白曉暢,不堆砌也不晦澀,即使不諳出處,亦能欣賞詞中意境,不致造成閱讀上的隔閡。如〈鵲橋仙?七夕〉:「今生鈿盒表予心,祝天上人間相見。」即是化用白居易〈長恨歌〉中的「但較心似金鈿堅,天上人間會相見。
」、〈攤破浣溪沙〉:「多少滴殘紅燭淚,幾時乾?」即是化自李商隱〈無題〉詩中的「春蟬到死絲方盡,臘炬成灰淚始乾。」雖是鎔鑄前人詞句,但渾化自然,仍能有自己的特色。
納蘭性德對於時空的隔絕、時間的消逝,常常有無限的感嘆,故常用對比的情境來相互映襯。
如〈尋芳草?蕭寺紀夢〉:「客夜怎生過?夢相伴,綺窗冷和。薄嗔佯笑道:『若不是恁淒涼,肯來麼?』 來去苦悤悤,準擬待,曉鐘敲破。乍偎人,一閃鐙花墮,卻對著琉璃火。」〈鳳凰台上憶吹簫?守歲〉:「錦瑟何年,香屏此夕,東風吹送相思。記巡簷孝笑罷,共撚梅枝。
還向燭花影裏,催教看、燕蠟雞絲。如今但、一編消夜,冷暖誰知。 當時。歡娛見慣,道歲歲瓊筵,玉漏如斯。悵難尋舊約,枉費新詞。次第朱幡剪綵,冠兒側、鬥轉蛾兒。重驗取、盧郎青鬢,未覺春遲。」這是除夕夜追憶前塵往事之作,今昔的對比交互進行著,排列的相當整齊。
前三句感概時光流逝,為回憶留伏筆。下四句寫從前相處的樂情景,以「如今但」驀然迴轉,映襯目前的孤單。過片寫從前心態,以為一切都可以長長久久,「悵難尋舊約,枉費新詞」以下,又拉回現實中來。「重驗取」三句,將今昔比並對照,作一收束。
納蘭性德自盧氏去世後,從淒切哀苦,尋求宗教慰藉失敗,到走向絕望寂滅,最後復歸於平靜,這便是其悼亡詞作所含思想情感的發展歷程。
納蘭性德的悼亡詞雖然取得很高的藝術價值,但詞境終究過於淒苦,反應於其中的思想又過於消極。造成如此局面的內再因素,主要是其自身的性格過於善感,而外在因素則不能不說是其生活環境和經歷的狹窄與侷限。
相关攻略
- 1 【黑道风云二十年电视剧第二部】《东北往事之二十年》定型海报5.1回顾展
- 2 【广州装修论坛】2016广州设计周“智能信息化使装饰界更加美丽”高峰论坛完美接待。
- 3 【康富来太阳能热水器】中国补血保健品市长/市场前景及市长/市场分析预测
- 4 【新房帮登陆】小说|李鹏:帮公公租房子。
- 5 【天翼十字绣图案大全】母亲节镜头瞄准了超级漂亮的妈妈,揭露了妈妈们对抗岁月的秘密。
- 6 【宁陕二手房】中韩最低工资标准出来了!这些地方会上涨
- 7 【北京窗帘价格】如何买合适的窗帘
- 8 【改版机和水货的区别】果粉请注意“水”4G与2G iphone 6和iphone 6 plus有何不同。
- 9 【人人折团购】十年过去了,单位终于第一次共同购买员工住宅,我激动不已,没想到最后会被坑
- 10 【东区音乐公园地址】刚来的时候,48小时缓慢地生活,很容易逛成都特色。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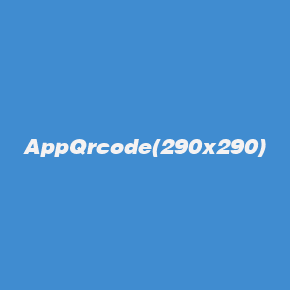 扫码下载安卓APP
扫码下载安卓APP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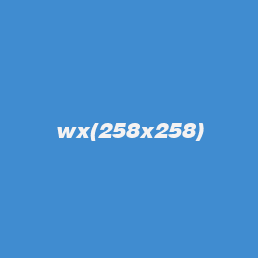 微信扫一扫关注我们
微信扫一扫关注我们
 微信扫一扫打开小程序
微信扫一扫打开小程序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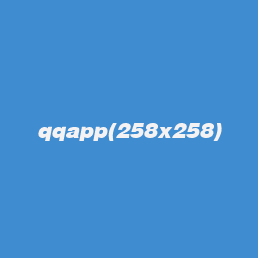 手Q扫一扫打开小程序
手Q扫一扫打开小程序
-
返回顶部

